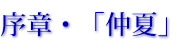
這是個常常出現在我夢中的情景。
那是個吹着涼風的,仲夏的下午。
在我們海邊的家中,幼小的我抱着一個很可愛的小貓布偶,靠在房間的門邊,聽着客廳中一個女性的話聲。
我向客廳裡望去,坐在木椅上的是父親,站在他面前不遠處的,便是那女人。
二人之間的氣氛很冷漠,但是説他們在吵架,卻又一點也不像。太安靜了。
父親只是聽着女人的話,一句話也沒回答。
然後女人走到我的房間,蹲下在我面前。她向我微笑,温柔地看着我。
她緊緊抱了我一下,然後走出房間。
之後我聽見了大門打開、關上的聲音。接着是長久的寧靜。
我的記憶裡,找不到那個叫母親的人的長相。
沒有母親的日子大約過了三年,父親帶着五歳的我離開海邊的家,到了一個很遠、很陌生的地方去。
在飛機上不知過了多久,我跟着父親到了一座小山丘上,停下在一家漂亮的木造平房前。
「從今天起,雨音,這兒就是我們的家。」
我們進了房子内。父親帶着我,走到客廳前的落地玻璃窗前。
在我眼前的,是玻璃窗外無雲的晴空,和一片無際的、平行的紫色和白色。
「紫色的是薰衣草……白色的是毋忘我。」
父親抱起了我,我還記得他那温柔的微笑。
「爸爸……這兒是什麼地方?」
我看着眼前的花田説。
父親看着我,微笑,一句話也沒説。
然後父親帶我到了屋外那片花田去。我看見那麼美麗的景色,完全忘了自己身在何方,只是高興地走進花田裡,一直向前走着,卻發現這片花田大得好像沒有盡頭似的。
走了好一會,父親笑着追上了我,於是我們就那樣躺在花田裡,享受着温暖的陽光,伴着包圍着我們的薰衣草的芳香,我覺得自己好像身處天堂一樣。
「雨音,妳喜歡這兒嗎?」
父親温柔的聲音傳來。
我笑着點頭。「喜歡!好喜歡!」
「那麼,以後我們就留在這裡好嗎?」
「好呀!」我很高興地點頭。
大學時代開始主修德語和美術的父親,在畢業後跟母親結婚之前,曾經在維也納住了數年。其實從來沒有太多人支持父親選擇在大學主修美術的想法,因為差不多所有人都認為,男孩子應該為自己的前途打算,夢想是不能超越現實的。然而父親在美術方面真的很有天份,在維也納的時候,一間有名的美術學校看中了他的作品,邀請他參加一個集體畫展,之後也有很多機會,讓父親總算踏出了達成夢想的第一步。
二十六歳的時候,父親返回東京,在當時上班的畫廊裡認識了常來的母親。交往了兩年後,兩人便結婚了。
那或許從一開始就是個錯誤的決定。兩個人的性格很不同,父親是為了夢想而生存的人,母親的想法卻相當現實。
我想,他們一定曾經深愛過對方,但最後還是發現,相差太遠的價値觀,並不是單靠愛就能彌補吧。
母親決定跟父親離婚的那一年,正好是父親的事業最失意的時候。然而母親作為應該是最了解他的人,卻沒有給他太多的支持。
離婚的事實使父親消沉了好一陣子。但他沒有像一般人借酒消愁,他只是坐在沙灘上,可以坐上一整天;又或者躲在工作間内,埋頭作畫。
到最後,父親終於振作過來,得到一位在維也納的朋友的介紹,父親決定到慕尼黑去發展。
可能是因為那時年紀還小,我很快便適應了德國的生活。最初因為語言不通,我在學校交不到朋友,但德國的小孩子很友善地接納了我,還主動教我德語。對那時候的我來説,那是非常大的鼓勵。
到了德國以後,父親的事業也漸漸順利發展起來。慕尼黑的風景很有名,父親因此專門風景畫,尤其是我們家望向外的那片花田,從不同的季節、時間和角度,他已經畫過不知多少遍。
而我除了上課以外,也開始學鋼琴、中提琴和聲樂。由那時開始,我發現自己非常喜歡音樂──就像父親熱愛美術一樣。
我的音樂老師Herr Wagner是德國人,是父親在維也納時認識的好朋友,也是非常有名的音樂家。他比父親大差不多十年,妻子也是德國人,同樣是在歐洲音樂界有名的指揮家。他們沒有子女,一直視我如己出。
十四歳那年,我認識了幾位在校外組地下流行樂團的德國朋友。他們那時正好缺一位鍵盤手,於是當他們知道我一直有學鋼琴之後,便邀請我也加入他們。
那時我對彈奏流行音樂一點經驗和信心也沒有。然而當我跟Herr Wagner提起這件事時,他卻很鼓勵我去試試。
「流行音樂跟古典音樂的確是很不同。不過以妳的天份,妳一定能將演奏古典音樂所學到的融入流行音樂裡,而且我已經沒有什麼可以教妳了。不過妳別忘了要繼續練習就好了。」Herr Wagner笑着這麼跟我説。
因着Herr Wagner的説話,我決定了要試一試。
樂團的名字叫Licht & Schatten, 即是光與影的意思。在樂團組成大約三個月後,我也開始擔任主音。直至上個月,父親終於決定,要回日本──東京去發展。
本來我是打算單獨留下來的,但父親不放心我一個人,堅持要我一起回去。就這樣,我跟着父親回到東京來──這個應該是我故郷的地方。